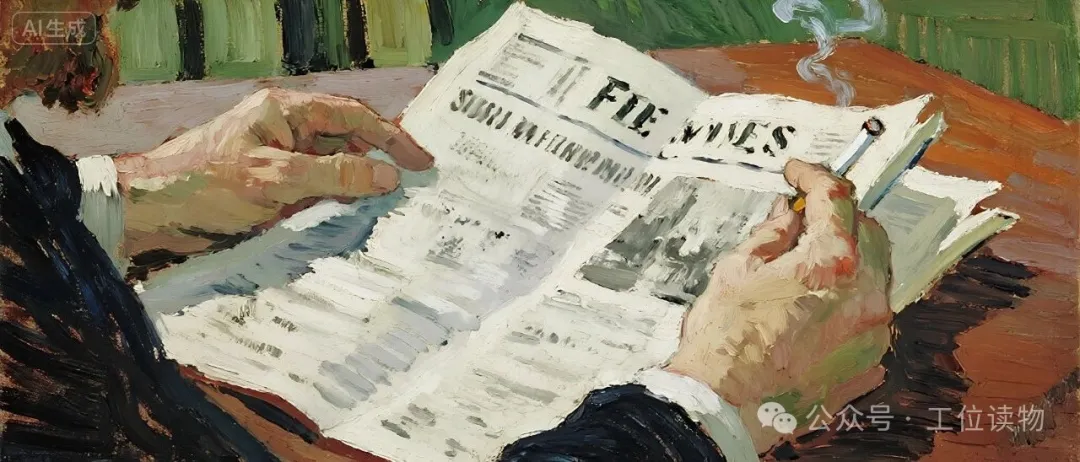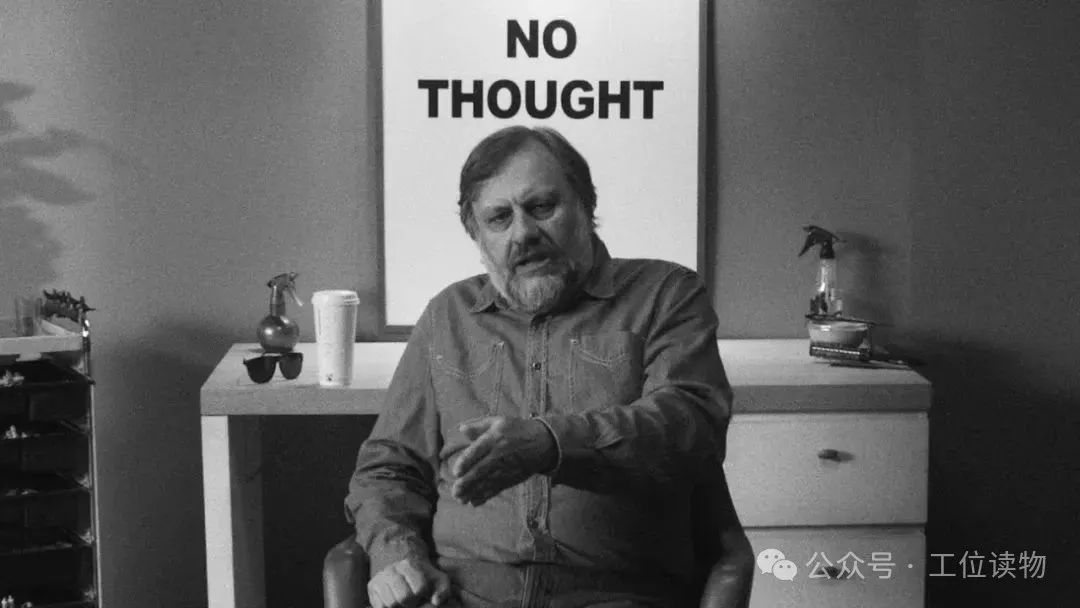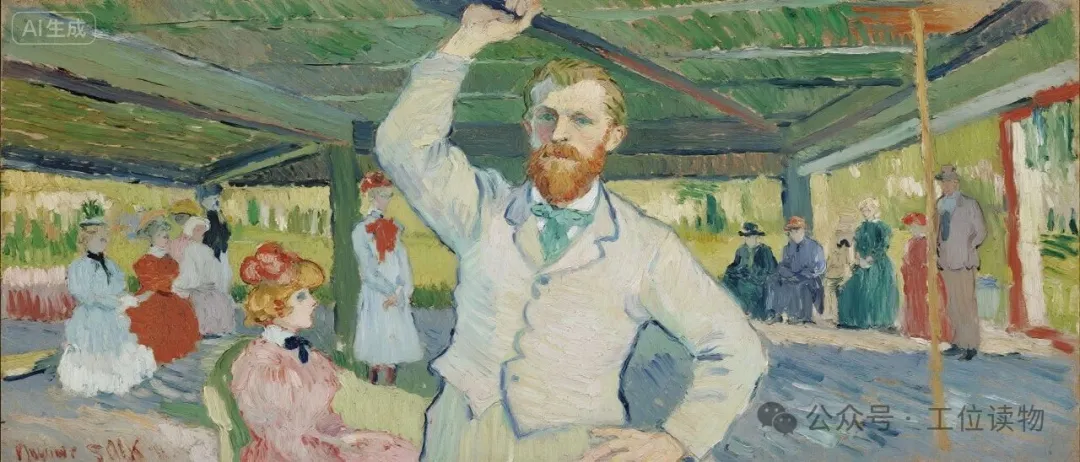| 男性应该少关注国际局势 | |
| www.wforum.com | 2025-07-16 12:53:54 公位读物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
|
|
|
|
|
|
|
|
今天在咖啡店里看书,碰见几位男性在一旁谈论国际政治。出于好奇我旁听了一部分,提到几个我比较熟悉的话题,发现他们的谈话里有价值的部分真的很少,大部分还是“犹太人掌控美国”“欧盟货币崩溃”“烟民养活航母”之类的网红观点。 相信读者只要还觉得自己年轻,尤其是女性读者,应该是比较反感那些在酒桌上谈论国际局势的中年男性的。可能说不上哪里觉得反感,但就是觉得不舒服。 最近在学习项飙的“附近”理论,我突然发现,如果把这些男性和“附近”的概念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他们不正就是离“附近”最远的人吗? 项飙在访谈中说过一个案例:在牛津和一些学生交谈,他们很难说清楚自己的人生和现状,甚至很难完整地叙述自己或者父母的生活经历,但是对全球危机、气候变化这种大话题却能讲很多。
项飙是这么认为的:对“附近”无法叙说的人,其实对世界的述说也是很无聊的。我觉得这也是这些男性的问题,他们如果不讲述那些无聊而情绪化的网红观点,那对全球局势这种复杂话题,他们也没什么可聊的。 男性们关心宏大叙事的抽象政治,最开始是为了充分理解经济、政治和金融,帮助他们作为一个传统男外女内家庭的顶梁柱做出符合时代趋势的决策。所谓“很有格局”只是这个需求的副产物。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对决策的需求开始转变为欲望,大部分时候,一个小家庭的决策者在判断国际局势时犯错的概率很大,所以对于“失败”的恐惧就转变成了对“格局”的欲望。这种被压抑的欲望通过酒桌上的夸夸其谈释放出来,成就了这种“抽象的大男子气概”(女性主义学者Nancy Hartsock)。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可以详细讲讲这种抽象男子气概的形成。
1.欲望就是恐惧 齐泽克在《享乐与虚无》中说,逆转的欲望本质就是缺失。对世俗成功欲望的压抑,转变为对压抑的欲望,实现欲望的阻碍恰恰是维持欲望的支柱。就像支撑着一段婚外恋的通常是背叛本身,大部分婚外恋者一旦真的与原配离婚,那么与第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破裂。
斯拉沃热·齐泽克 齐泽克认为,这种欲望的逆转,在我们所处的消费社会里,位于资本主义逻辑的核心地带。我的理解是,也正是这种逆转的欲望,使得消费型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品被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诞生,源于资本获取利润时反映在计算收益(数钱)行为上的快感,而在获取利润本身有困难时,快感发生了逆转,数钱本身成了一种快感。在精神分析学基础理论(弗洛依德)认为,我们渴望的并非我们欲求之物,潜意识最底层的欲望通常都表现为我们不想看到的东西,也就是恐惧。 结合起来就是: 我们恐惧赚不到钱,所以我们爱上了数钱; 男性恐惧无法成功,所以他们爱上了谈论成功。 2.从关注大局到关注附近 关注身边的案例,我会有一个观察:国际局势越是不确定,周围的男性就越喜欢高谈阔论国际局势。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论证了我上面的看法,即:表现大格局的欲望来源于对国际局势变化的恐惧。其实,因为地区冲突变得越来越频繁,经济和货币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精密,想要以一个非专业者的角度去预测国际局势也越来越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就没有意义,这也是我建议男性朋友们少关注国际局势的原因,它没有太大用处了。但是关注“附近”的用处却是越来越大的。 台湾社会学者郑珮宸在《台湾社会学刊》上发表的《改革公园儿童游戏场的妈妈民主:连续照顾日常与倡议论述的对抗性公共领域》拆解了女性主义学者弗雷泽的“公共领域”理论,指出一种最直接的落实“附近”的切入点:重建被忽视的公共领域。
女性主义学者 南希·弗雷泽 这其实很好理解,举一些例子就能知道:让商场都有干净的母婴室;扩容女厕所减少排队拥挤。宏大一点的例子:让建设指标可以随人口流动跨省交易,让大城市的外来务工者都可以很在城市里找到廉租房,安置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优化户籍和社保制度,提升地区经济集聚效应,同时可以给到大城市更多第三产业就业容量。 这些改造具象的“附近”的方法,都是可以实打实让人触摸到“附近”的通道。思考并呼吁这些事,在这个逆全球化的时代,比思考国际局势要有用太多了。而很可惜,我读到的思考这些具体方法的著作,大多数都来自女性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舆论中谈论具体“附近”的也大多是女性,男性真的很少思考这些具体而有用的事。
这也是我觉得应该呼吁男性少关注国际局势的原因,男性真的离“附近”太远了,关注的事情实在是太遥不可及了。其实在“附近”这个话题上,女性主义已经做出了很多批判和超越,女性叙事里对自身内在和他人主体的关怀是随处可见的。或者说,一个女性只要具备女性特质,稍微有一些文化水平,她们甚至是很容易脱离出“附近”缺失带来的陌生感的。 但反观男性,传统的大男子教育让他们很难脱离世俗对成功的定义,虽然男性总是表达出自信、无畏、理性,好像很强大,一般一个女孩儿对男朋友最好的表扬大概也就是“情绪稳定”,这在这个焦虑的社会里也显得很强大。但其实男性是需要很多“逆转的欲望”去堆砌这种“强大”的,也需要很多更“弱小”的女性去陪衬这种“强大”。 这种“强大”在谁都没法依靠个体力量存在的逆全球化时代是很难实现的,事实上,越是在这样的时代也就越容易实现男女平等,大男子叙事在下行周期里很难对女性主义叙事做出超越。
3.结语 前面写过一篇《少看卢克文》,其实已经包含了我在这篇文章中的思考。但是对单一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很难写明白群体心理的内核,也很难去定位群体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变迁,我觉得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好像想得更清楚了。 综上,也许之后“少看”这个系列,以后我会继续关注现象的内核,尽量不只针对具体的人物,之前的内容大纲也会发生改变,所以敬请期待~ |
|
|
|
|
|
|